光里的奶奶

本网讯(常红锋 林娜)时间过得真快,奶奶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三年了。九百多个日日夜夜,就像门前那条小河,静静地流走了,却在我心底留下一片永远湿润的河床。这段日子里,我很少能在梦中与她相遇,这让我时常感到些许失落。人们说,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风雨,而是一生的潮湿。这话说得真对。那种潮湿,不是倾盆大雨后的泥泞,而是梅雨时节若有若无的湿润——晾不干的衣裳,摸起来总带着些许凉意;就像心底总有一块地方是柔软的、湿润的,轻轻一碰,思念就会悄无声息地漫上来。
人们也说,逝去的亲人不常入梦,是因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,也想让你放下牵绊,在这人间过得更好。我想,奶奶定是这样希望着的。她从来都是这样,宁愿自己默默承担所有,也不愿我们为她多难过一分。她的爱,从来都是给予,而不是索取。
提起奶奶,我总会先想到爷爷。爷爷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,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他背着那个磨得发白的药箱,走遍了附近十里八乡的每一个村落。他一辈子仁心仁术,深更半夜被人叫醒出诊是常事,可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乡邻们敬重他,这份沉甸甸的敬重,也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了奶奶身上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奶奶虽然不识字,却是爷爷最得力的“助手”。谁家媳妇要生了,她会收拾些干净的旧衣裳送过去;谁家老人病了,她会熬一锅小米粥端去。她常说:“你爷爷治的是病,咱们能帮的,是心。” 这话简单,却道尽了她一生的为人。
我童年最鲜活、最色彩斑斓的记忆,便是奶奶带着我去赶集。那时的集市,是我整个世界的缩影,充满了各种新奇的声音、味道和景象。天还没大亮,奶奶就会轻轻把我摇醒,往我嘴里塞一小块冰糖。我眯着眼睛,任由她用温热湿润的毛巾给我擦脸,然后牵着我的手,踏上那条通往集市的、露水未干的小路。
集市上真是人声鼎沸啊!卖一些头花和手镯的、卖各式各样小吃和小玩意儿的,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、熟人见面寒暄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热闹得像一锅煮沸的水。她温暖干燥的手总是紧紧攥着我,生怕我被人流冲散。我那时个子矮,视线所及,尽是大人们的裤腿和摆满货物的摊子,鼻子里充满了泥土、蔬菜、油炸点心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的、独属于集市的气味。
集市里总会有熟识的面孔热情地迎上来,离得老远就听见那带着乡音的、亲切的呼喊:“孙医生家里的!” 然后便会拉着奶奶的手,唠上好一会儿家常——家里的收成、孩子的功课、老人的身体……奶奶总是微笑着,耐心地听着,适时地点头,或轻声安慰几句。她那时的笑容,是我后来在很多年里都难以准确形容的——那里面有作为“孙医生”妻子的自豪,但更多的,是一种发自内心的、朴素的谦和。她从不因这份敬重而显得高高在上,反而更加平易近人。
唠完家常,对方总会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,往我手里塞些东西——一把刚炒的花生,几个新摘的柿子,或者几块用花花绿绿糖纸包着的硬糖。最神奇的一次,有位卖山货的老爷爷,非要把笼子里一只瑟瑟发抖的小刺猬送给我。那小刺猬蜷成个球,棕灰色的刺看起来吓人,摸上去却是软软的,一点也不扎人。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头,轻声说:“快谢谢伯伯。”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竹笼子,像拥有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。那只小刺猬后来去了哪里,我早已记不清了。或许是被奶奶悄悄地放回了山野吧。然而,记忆里永远清晰的,是奶奶那只因常年劳作而粗糙、却无比温暖安心的掌心的温度,和她在集市上遇见每一个熟人时,那自豪又谦和的笑容。那笑容,像秋日里的暖阳,不耀眼,却足以照亮我整个童年。
每年我生日,奶奶总会从乡下来到城里为我庆生。天刚蒙蒙亮,甚至星星还挂在天边,她就已经起身了。她会去鸡笼里拣出来新鲜热乎的鸡蛋,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,用麦秸秆仔细地垫好,放进竹筐里,直到装满沉沉的一筐。她确保每一个鸡蛋都被妥帖地安置好,一个都不会在颠簸中破碎。然后,她就要提着这筐鸡蛋,赶最早那班大巴来城里。半梦半醒的懒觉中,已经听见奶奶已经和妈妈在客厅拉起了家常,我兴奋地跳下床跑进奶奶的怀里!奶奶笑弯了双眼,蹭蹭我的脸蛋说:“俺家小乖睡醒了!今天过生呀!”还没好好歇一会呢,就钻进了厨房,开始为我煮一碗长寿面。面是她亲手擀的,劲道爽滑;汤头是用老母鸡熬的,金黄清亮;最上面,必定卧着两个圆润饱满的荷包蛋,像两轮小小的、温润的月亮。她坐在我对面,就那么看着我,催促着:“快吃,趁热吃。” 那时我只觉得,这是全世界最香的面,最香的鸡蛋,狼吞虎咽,风卷残云。我从未想过,那一筐鸡蛋有多沉,那一路的颠簸有多累,那一片深沉的爱,有多不容易。我说城里什么都能买到,超市里鸡蛋又多又便宜,让她别这么辛苦。她总是固执地摇摇头,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:“外面的,哪比得上家里的。这是咱自家鸡下的蛋,有营养。”
后来,爷爷退休了,爷爷奶奶便搬到了城里,上高中的时候过星期都要去看望他们。每次到奶奶家,她总会像变戏法一样,从柜子深处掏出她珍藏了好久、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点心——或许是叔叔从外地带回来的桂花糕,或许是她赶集时买的、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蜜三刀。点心往往都有些受潮变软了,可她看着我吃时那满足的眼神,比任何点心都甜。
临出门时,奶奶总要悄悄把我拉到里屋,关上门,然后从贴身的衣兜里,掏出那些不知攒了多久的钱。那些钱,面额不等,带着岁月的痕迹,皱巴巴的,却被她叠得整整齐齐。她用力地、近乎固执地硬塞进我的口袋,紧紧按住我的手,不让我掏出来。“拿着,上学多买点好吃的,好好学习呀”她低声说,“别告诉你爸”。奶奶这推辞不得的爱,沉甸甸的,我羞涩地收下,心里暗暗发誓要更努力地学习,以后赚钱给奶奶买更多好吃的!
每年最热闹的大日子就是奶奶的生日。一大家子人,从四面八方赶回来,围坐在那张老旧却结实的大圆桌旁,欢声笑语几乎要掀翻屋顶。姑姑们在厨房里忙碌,爷爷爸爸高谈阔论,我们这些孩子则在屋里屋外追逐打闹。奶奶就坐在主位上,穿着或许是我妈妈或者姑姑给她买的新衣裳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看着满堂的儿孙,脸上洋溢着一种无比满足的光彩。吹蜡烛前,我们总要她许愿。而她的生日愿望,年年如此,朴素得让人动容,也让人心疼。她总是双手合十,闭上眼睛,很认真地说:“我一愿,咱们全家人,大大小小,都健健康康,平平安安。二愿,“你们这些当医生的,都能把病人的病给治好,像你爸一样。”
她的心里,装的永远是这个枝繁叶茂的大家庭,和她所理解的、与爷爷一脉相承的“医者仁心”。她没读过多少书,讲不出什么大道理,但她用最朴素的方式,践行着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古训。她的世界不大,就是这个家和附近的乡邻;她的世界又很大,装下了所有她认为需要关爱的人。
然而,生命的无常,从不会因一个人的善良而网开一面。没能送奶奶最后一程,是我心里一个永远填不上的缺口,一道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的旧伤。那时正赶上疫情封校,记得那是个雨天,我和同学撑着伞在去餐厅的路上,接到了爸爸的电话,告诉我奶奶已经走了。瞬间,整个世界的声音仿佛被抽空了。接着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恨自己为什么离家这么远,恨自己为什么总觉得来日方长。
每次翻看相册,看到奶奶精神矍铄的模样——她抱着小孙子、小孙女,笑得分外慈祥;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眯着眼睛打盹;她站在灶台前,正准备一大家人的饭菜……这些定格的瞬间,总让我内心的潮湿开始剧烈地翻涌,化成止不住的泪水。我总想着,如果能再见一面,哪怕只有一分钟,我要告诉她很多很多事——奶奶,我毕业了,拿到了那个红彤彤的毕业证书,要是您还在,一定会戴上老花镜,用手摸了又摸。奶奶,我工作了,能自己挣钱了,可以给她买更软的糕点、更暖的衣裳了。奶奶,我现在也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了,我会永远记得您的教导,好好学习,用心看病。奶奶,我学会做饭了,虽然远不如您做的好吃,但也能做几个像样的菜了。奶奶,大家都挺好的,就是,很想您。
而最重要的,是那句我一直以为有机会说,却最终没能亲口说出来的话:奶奶,谢谢您。谢谢您,让我从小就是个在爱里长大的幸福的小孩;谢谢您,用您的言传身教,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善良与付出;当您的孙女,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和幸福。这句话,在我心里排练过千百遍,却终究,没能当着她的面说出口。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。
这种沉重的思念和遗憾,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,直到很久以后的那个梦的出现。梦里的场景非常清晰,却不同于我记忆中的任何一个场景。那是一个清晨,薄雾如纱,阳光是金色的,温柔地洒满大地。奶奶,不再是那个头发花白、腰身佝偻的老人,而是一位少女的模样,大约十七八岁,穿着素净的月白衣衫,黑色的长裤,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垂在胸前。她的脸庞光洁,没有一丝皱纹,眼睛明亮得像山涧的泉水,笑容干净、灿烂,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、属于少女的羞涩与轻盈。
她就站在那片晨光里,身后是模糊的、泛着光晕的田野。她回头,朝我们用力地挥了挥手,脸上绽放出那个明亮无比的笑容。没有言语,但那笑容里,充满了安慰、释然和告别。然后,她转过身,步履轻快地,向着那片越来越明亮的光里走去,身影逐渐融入光芒,直至消失。醒来时,我发现枕边湿了一大片,但奇怪的是,心里那块压了许久的大石头,仿佛被挪开了。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快感和温暖感,包裹了我。我忽然明白了,奶奶终于卸下了岁月的重量,卸下了一生为妻、为母、为祖母的辛劳与牵挂,变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、轻盈的少女。她往光里去,不是消逝,而是回归,是奔赴另一种安宁与自由。
这场景,莫名地让我想起那些年,她为了给我过生日,总是最早赶上那班开往城里的车。她步履匆匆地走向车站,走向我,仿佛也是走向一片光——那片光里,有她惦念的孩子们。她往光里去,就像那些年,她总是把最新鲜的爱,最早送到我面前。
如今,我们全家商量着,想为她出一本薄薄的书。不是因为她的故事多么传奇伟大,足以载入史册;恰恰相反,是因为她太普通了,就像亿万中国女性一样,默默无闻,却用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,温暖了一个家,滋养了几代人。我们害怕,害怕这些细碎的温暖,会被时间的流水冲散;我们想让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被记住、被传承。
我们想用文字告诉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:看,这就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奶奶,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。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,但她用最朴素的方式,倾其所有地,爱了她的孩子,爱了孩子的孩子。她的爱,融汇在一碗长寿面里,凝结在几块舍不得吃的点心里,折叠在那些皱巴巴的纸币里,闪烁在她每一次自豪又谦和的笑容里。这种爱,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血脉相承的根基。
我想,当书页被轻轻翻动,发出的那种“沙沙”声,大概就像当年她挎着竹篮,走在故乡田埂上,风吹过两边绿油油庄稼地的声音吧。那是一种宁静的、充满生命力的声音。而我们写下的这些文字,是我们替她攒下的另一筐“鸡蛋”。每一个字,都像她用麦秸秆垫好的鸡蛋一样,被我们小心安放;每一个字,都盛着一份完整的、不曾破碎的思念。
奶奶,你在光里,都看见了吗?
我们想你,一直,一直。在这绵长的思念里,你也一直,一直都在。在记忆的光里,在每一个被爱唤醒的清晨。(作者:孙笑莹)
文章摘自孙世长《我的母亲》之书:
作者孙笑莹简介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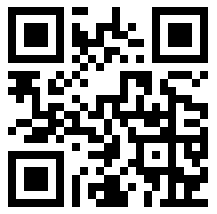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